记一次医院探访
我围抱着火炉,
烤热漫长一生的一个时刻。
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,
我其余的岁月,
我的亲人们的岁月,
远在屋外的大雪中,被寒风吹彻。
—— 刘亮程《寒风吹彻》
同事 K 生病了,那是上周四的事了。当时下午上班的时候,他提出来说实在撑不下去了,想请假回家休息一下。当时以为是感冒,所以在他第二天依然请假的时候,还有点奇怪。我也经历过感冒。因为体质好,一般的感冒在初期症状就消失了。一些重感冒确实比较难受,但从我记事起,就没有因为感冒发烧去过医院(当然不建议这样,实在不舒服,还是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的)。心里还有对他的一点嘲讽,“有点虚啊,小伙子!”
周六在家玩游戏,看电视。中午收到 K 的微信语音消息,说让我过去陪陪他,他住院了。我想你去医院挂点葡萄糖和盐水就好了,住院有点...还有就是要我过去陪他,确实不太想,一方面我觉的他的情况不需要,另一方面不想打断宅在家里看电视、玩游戏的悠闲生活。心里对他有些不满,一个感冒发烧就虚成这样。
周六晚上的时候,我们部门领导出动了,组了一个群聊,拉了我和另一个住在附近的同事,准备第二天去看看他,慰问一下。我想也行吧,同事一场,生病住院了,买点水果探望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并且,医院离住的地方不远,走过去,送一下水果,说几句话,大概也就回来了。虽然领导说不用带东西,但我还是早早起来去楼下超市买了点。附近是有家花店,但考虑到太早花店不一定开门,还有就是花没有什么实质价值,又是男同事,没必要,就没买。
早上的凉风吹在身上,很舒服。按照导航步行大概 10 分钟就到了他的病房。比较现代化的病房,有独立卫生间,就是床有点小,如果是我睡的话,夜里翻身可不行。窗户开着,没注意窗帘,外面的是旁边建筑的屋顶,上面是一些中央空调外机。一间病房有两张床,床的左侧都摆放了一张床头柜,靠门的墙上有一个壁橱,两开门。而两张床前的空间摆了两张折叠床,大概是方便陪护人晚上短暂休息的。K 的床头柜上摆放了一台机器,拖出一根电,连接在他的食指上。机器上面展示的几段像心电图一样不断跳动的波形图。他的脸色不太好,调侃了他几句,我就站在窗边吹风了。过会儿,昨晚陪夜的同事来了,西装革履的打扮,应该是昨天参加完展览就过来了。虽然他不算白,但还能勉强看出来眼袋有点重。聊了一会儿,得知好像是慢性肠炎,这两天一直在拉肚子。而且还要转院,陪夜同事打了 120 ,和之后陆续到来的同事跟领导去了另一家医院。我和陪夜同事坐的是救护车。下车的时候,听到急救的人惋惜的说,这么年轻就得了尿毒症,我才突然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。
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,之前的调侃,现在看来像是嘲讽。有点惋惜,然后就是等待了。下午的时候跟另外的同事、领导帮他缴费拿药,送血检、尿检样本。中间的时候有些无聊。急诊部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,但没有笑容。有的两三个聚在一起聊着什么,有的是坐在走道的急救病床上,有的在吃东西。急救部门外有些抽烟的人,烟丝四下飘散,很快没了踪迹。急救抢救室的大门时不时的打开,接着就是呼唤病人家属的护士的声音。从中午到晚上,也会有救护车的声音不间断地到来,急救部里面会出来几个穿着特殊制服的人过来抬担架。有些抢救过来了,有些没有,没有的就会有病人家属的恸哭。K 的母亲晚上 9 点多到了,领导去接的她,短暂的探望了一下,然后就跟我们回去了。领导让她先休息一晚,第二天我们要上班,不能陪护,之后的陪护工作会交给她。
回来的路上,晚风吹拂,依然很舒服。旁边的 K 的母亲一直不说话,只有我们问她的时候才会答一句。同事把我送到家的附近。走在路上,周围灯火不断,但很安静。静下心来,忽然有限惶恐。不是因为今天的探望,也不是急救部的在我眼前消逝的生命,而是我突然意识到的自己对生命的无感淡漠。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,是因为我的职业让我习惯了枯燥乏味,还是我成长经历让我看淡了世间冷暖?不知道,因为,那仅有的一点惶恐也消逝了,随风消逝。
本作品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许可协议 进行许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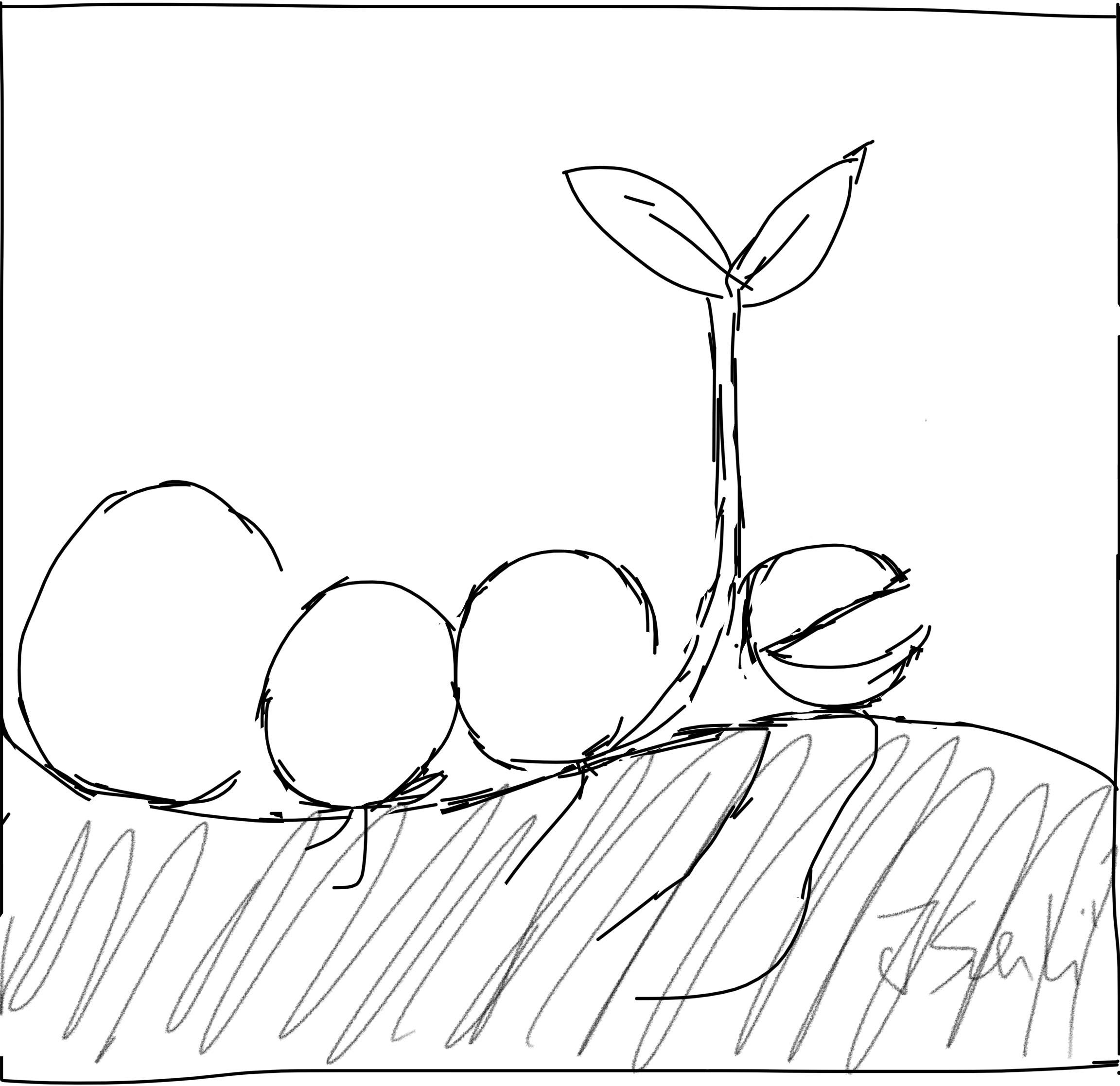 海滨擎蟹
海滨擎蟹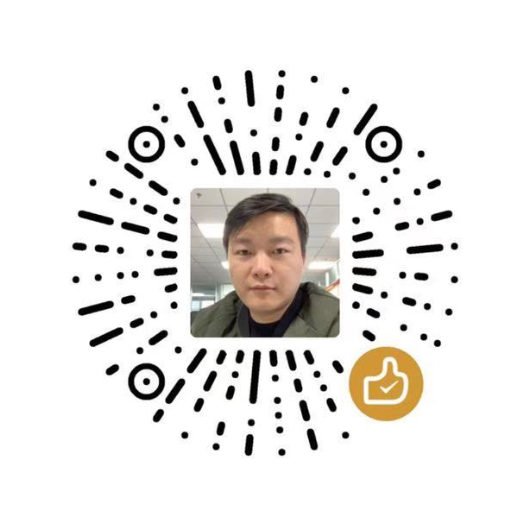 微信
微信 支付宝
支付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