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候的我
没有一点点的防备,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。

这是二姨家里整理清洁时发现的,我家小时候的照片都在 2005 年搬家的时候遗失了,或者就是保存不善,被销毁掉了。
一张照片,映照一个时代。这应该是出生十几个月照的吧,没什么印象了。
可能是太小的原因,我小时候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。有些甚至不知道是爸妈跟我讲的还是我自己的记忆,有些许混乱。
襁褓中的落水
记忆里对有着倒斗的拖拉机有深刻的描绘。农忙时能装东西,出远门可以在上面加盖篷子,防雨防风,一车能载好多人。坐在铺着稻草和棉被的车里,看着不断倒退远去的路,听着拖拉机不断的“突突”轰鸣声,特安逸,特想睡觉。
我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雨夜里。当时天下着瓢泼大雨,大姨夫开着拖拉机,载着亲戚好几家人,走在那种窄窄的“大堆”路上(当时兴河道改建,在河道的两边就是这种堆得很高的大土堆路),不知道去哪里。大姨夫夜里又累又困,再加上这样恶劣天气,视野模糊不清,一不注意就把拖拉机开到了“大堆”下的河里。河水倒灌进来,浸湿了棉被和衣裳,雨水也趁机侵袭,一车人就这样醒了过来。接着就是大人的叫喊声,小孩子的哭闹声,以及连绵不断的淅沥沥的雨声。当时的我还裹着厚厚的抱被,老爸和几个姨夫叔叔为防止拖拉机继续下沉,准备人力拉拖拉机上来。情急之中,我被甩上了岸。等到危机过去之后,爸妈突然想到了我,就去找我,还好找到了。来不及高兴,就发现我呼吸微弱。然后就是急诊,这家医院跑到那家医院。情况不太乐观,当时太小,正常的治疗手段很局限。比如说挂盐水,手臂上的静脉太细,几乎找不到,只能从脑门上扎针。医生很难判定是什么引起的,这就引起了家长的恐慌。我妈就是从那时候天天向耶稣祈祷,然后加入基督教的。
死神当然没有带走我,但脑门上的坑,我妈的信仰改变了。
水中的“野鸭子”
人都说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加上我嘴下面一颗痣,俗语云:“一痣在嘴,有汤有水”,我从小就带着“这辈子不愁吃喝”的期望。本来就比较受宠,加上又是家里的老二,家族里的长子长孙,没有理由的,我成了一只被放养的“野鸭子”(主要是大人也忙,没时间管)。
当时在拆迁,将原来的散户聚集到一个村子里。印象中在二爷爷家的老房子里(当时是买了他家的房子,然后拆迁为了拆迁款跟他家闹了好久的矛盾)住了好长时间。当时都是泥瓦房,四面墙壁都是用泥巴和着稻草建的。我家在中间,两边是姥太家(爷爷的妈妈)和一个跟爷爷同辈的有点亲戚的长辈家。三家围在一起,中间是一片空地。再往外是一条小路,路的两边栽了两排树。路的另一边是一条大河,印象中很宽,也很深。在夏天,那条河就是我的乐园。
那时候下河洗澡喜欢光着屁股,但因为到了知羞耻的年纪,所以在下河之前都是在路边左顾右盼一番,发现没人后,迅速地脱下短裤扔在岸边,然后跳进河里。爸妈一般都会有一人过来看着的,但有时确实太忙,就会让我先去洗,不准往河中间游。这样的话对我一个好动又无知无畏的小孩子是没有约束力的,先是在靠近岸边的地方用双脚打着水花,待发现没有人过来看着时,就掉头往河中间游了。
那时候的我真的可以说很“骨感”。本来就营养不良,在加上男孩子好动顽皮,吸上一口气,可以肉眼去数身上的肋骨,肋骨下的肚子还会凹进去好大一块。那也是我的一个绝技,每逢有人来家做客,都要拉起上衣露出前胸和肚子,上前表演一番。虽然很瘦,但身体很壮,在河里游泳,游一个多小时不费力,可以从下午4、5点一直游到太阳落山,还很兴奋。在水中的我是自由的,可以狗刨,也可以仰泳,也很擅长“扎猛子”,一个“猛子”可以到水下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因为水底站不住脚,所以有时候还会抱着河边一块石头沿着河岸向深水处走。有时候会游到对岸去拔一株芦苇,然后再芦苇叶子一片一片地扯下来,扔在水里。有时候累了,就把身体放平,耳朵里灌着水,听着水流的声音,人就这样随着水波漂浮。每次上岸后,手脚的皮肤都会发皱,有时还会感到寒冷。但这些并不会阻碍我的乐趣,用水冲一下,擦擦身体,穿件衣服就好了。
水鸭子也有上岸的一天,随着我的上岸,那个童真童趣的我再也看不到了。
“姥太”家的粥
“佬太”是我们那边对爷爷的母亲的称呼。那段时间的相处,使我们成为了祖孙辈最亲密的人。“佬太”当时是个七十几岁的老人,但依然自立更生,自己照顾自己。有时她也会代替我爸妈去看着我游泳。但印象中,她是一个很温柔很体贴的老人。因为住在旁边,所以她跟我爸妈经常会唠我听不懂也听不进去的家常。虽说是很亲近的关系,但我们还是分开吃饭的。当时我们两家共用一个厨房,我们叫它“锅屋”。就是一个小房子,里面架了一、两口铁锅,燃料用的是树枝,麦秸秆之类的,然后会有一根烟囱通往屋外。午饭时分,烟囱就会持续不断地吞云吐雾,还会有锅铲跟铁锅摩擦地“咔吱咔吱”的炒菜声音。用大铁锅烧饭是很香的,特意多烧一段时间烘烤出来的锅巴也会一绝。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早晚的粥。铁锅加热快,散热也快,煮好的一锅粥过一段时间就能拿瓷碗乘了。这就要讲到我的另一个绝技了。一大碗稀稀的凉好的粥,在我从厨房走到饭桌前,就能被我给消灭掉。然后又是一大碗。一般我会足足吃上三大碗的粥才肯罢休。“佬太”家腌制的咸鸭蛋也是一绝,蛋黄松软细腻,用筷子轻轻一戳油花就止不住地往外冒,忍不住会用舌头一圈又一圈地舔。这也是我“叛逃”到她家吃饭的原因,咸鸭蛋跟凉好的白米粥真是太绝配了。
在那段时间之后,再看到“佬太”,一切都变的不同了。她一直躺在床上,床上是厚厚的棉被,身上也穿着厚厚的棉袄,眼睛浑浊,不时会有眼泪流出,然后她就不时地擦拭一下眼角。开始一段时间她还能认出我来,之后思维也比较混乱了。她会拉住我的手,一句接一句地讲述过去的一些人,一些事。在我高考复读的那一年,她离开了,我没能去看最后一眼,之后的丧葬我也没有参加。
尾声
年幼不知畏惧,不懂感恩。光阴岁月,失去了一些东西,也留下了一些东西,那时候天真童稚的我已不复存在,这大概就是成长吧。
本作品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许可协议 进行许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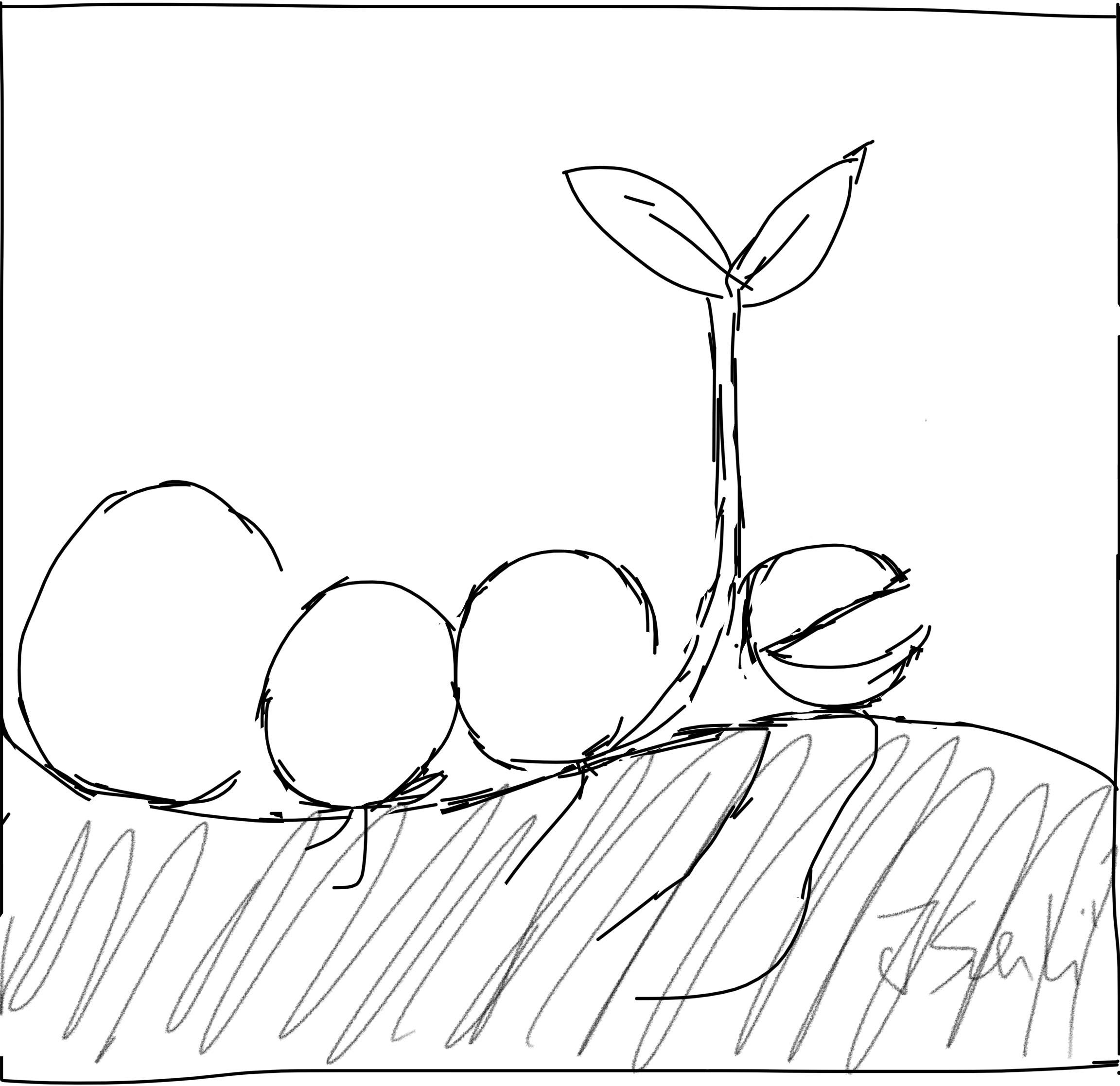 海滨擎蟹
海滨擎蟹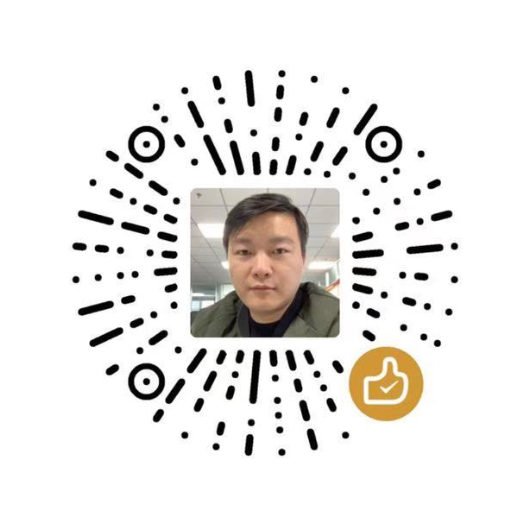 微信
微信 支付宝
支付宝